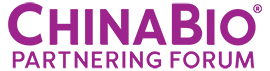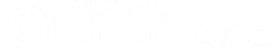近日,在生物医药创新的前沿阵地,百奥几何(BioGeometry)斩获关键成果,于蛋白从头设计领域实现重大跨越。公司成功向一家头部药企交付经可溶化改造的跨膜蛋白分子,且该成果已顺利通过功能验证,为药物研发注入全新动力。
2025生物医药产业大会了解到,这一突破的背后,是百奥几何自主研发的生成式 AI 大模型 GeoFlow 的强力支撑。凭借这一前沿技术,科研团队创新性地对跨膜蛋白的疏水跨膜区进行从头设计,打破常规。改造后的跨膜蛋白能够稳稳扎根于水溶液中,以稳定的单体形式存续,关键是还完整保留了自身的结构与功能特性,就像是给原本 “水土不服” 的跨膜蛋白找到了适配水溶液环境的 “生存密码”,一举化解了跨膜蛋白在水溶液稳定性与功能性之间长久以来的矛盾冲突。这不仅为高通量药物筛选凿开了一条全新技术通道,更为后续跨膜蛋白靶点研究以及药物发现工作全方位铺平了道路,开启了新篇。
一、跨膜蛋白研究困境:阻碍重重
跨膜蛋白,作为细胞膜上的关键 “守门人”,又被称作整合膜蛋白,在细胞膜磷脂双分子层中牢牢扎根,实现细胞内外的信息与物质交流,占据膜蛋白总量的 70% – 80%,是生命活动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要素。从功能维度细分,跨膜蛋白涵盖 G 蛋白偶联受体(GPCR)、离子通道、转运蛋白及其他各类受体等多种类型,肩负着维持细胞结构稳定、精准运输物质、快速传递信息等诸多重任。
然而,人类健康的 “宿敌”—— 众多疾病,往往与跨膜蛋白的功能失常紧密相连,这也让跨膜蛋白当之无愧地成为理想的药物靶点。当下,在已知药物靶点的 “版图” 中,以跨膜蛋白为靶点的占比已然超过 60%,而在抗体药物靶点领域,这一比例更是逼近 90%,足见其在医药研发前沿的核心地位。但跨膜蛋白的研究之路却布满荆棘。
其跨膜区与生俱来的高度亲油疏水特性,仿佛一道 “紧箍咒”,使其在水溶液中难以稳定立足。体外制备时,面临表达量低的困境,如同难产一般难以高效产出;纯化更是难如登天,多个疏水区域致使其在溶液中溶解度欠佳,极易抱团聚集,活性也随之丧失,而且跨膜次数越多,疏水跨膜区随之增多,制备难度呈指数级攀升;再者,其结构好似精密复杂的 “迷宫”,多个跨膜区域、环状构造以及糖基化修饰等,都让制备过程充满技术挑战。
2025生物医药产业大会了解到,传统的去垢剂和脂膜解体方法试图 “破局”,却因成本高昂,且在免疫动物或体外筛选进程中,常常对蛋白质结构造成 “致命伤”,导致功能丧失,无法为抗体筛选或跨膜蛋白功能研究提供有效助力,使得跨膜蛋白的结构解析、功能探究以及药物发现成为生物学领域的顽固难题,给免疫学研究与药物筛选工作蒙上厚重阴影。
二、破局之策:AI 驱动跨膜蛋白可溶化改造
百奥几何另辟蹊径,祭出技术 “利剑”。其技术方案宛如一场精细的 “分子手术”,首先精准固定跨膜蛋白的胞内与胞外区域,紧接着让 GeoFlow 生成式 AI 蛋白大模型大显身手,针对亲油疏水的跨膜区展开水溶化的从头设计。一番 “雕琢” 之后,成功构建出能在水溶液中安然 “栖息” 且胞外区功能完备的跨膜蛋白序列,令人惊叹的是,此时跨膜区与原始序列的相似度仅为 22.6%。GeoFlow 大模型更是展现出超强实力,即便在虚拟筛选阈值极为苛刻的条件下,依旧能比现有模型斩获更高的序列设计成功率,巧妙设计出不易聚集、稳定性超群,且胞外区功能稳如泰山的跨膜蛋白序列。
2025生物医药产业大会了解到,这一开创性技术平台,如同在跨膜蛋白研究的 “荆棘丛” 中开辟出一条康庄大道,不仅冲破了跨膜蛋白可溶化改造的技术瓶颈,挣脱传统方法在维持蛋白稳定性与功能方面的 “枷锁”,还为跨膜蛋白类抗原的高通量抗体筛选、从头设计以及药物发现筑牢全新的技术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百奥几何抗体项目负责人感慨道:“传统抗体发现与筛选手段在跨膜蛋白这一特殊‘堡垒’面前,显得力不从心,筛选效率极其低下。而生成式 AI 技术恰似一场及时雨,为抗原改造带来全新契机与破解方案。”
要知道,抗原制备可是研发抗体药候选分子的 “敲门砖”。有了设计出的可溶膜蛋白助力,百奥几何得以实现高通量、高可靠性地验证从头设计的抗体分子,大幅削减湿实验所需的时间与成本开支。这意味着科学家们从此能够在药物研发的 “战场” 上,更加高效、精准地筛选出亲和力与特异性双高的抗体,药物研发的效率与精准度都将得到质的飞跃。
三、战略意义:重塑生物医药研发格局
跨膜蛋白在神经系统、免疫系统以及代谢通路等生物学关键进程中扮演 “主角”,自然而然地成为探究生命活动、挖掘药物、攻克疾病的核心靶点。以 G 蛋白偶联受体(GPCR)为例,这类参与诸多生理活动的跨膜蛋白,是近 34% 的 FDA 批准药物的靶点 “担当”。尽管近些年来治疗性单克隆抗体(mAb)发展迅猛,但以 GPCR 为靶点的治疗性单抗研发却如同深陷泥沼,进展缓慢。截至目前,仅有两款 GPCR 单抗药物获批上市:用于治疗淋巴瘤的 CCR4 单抗(mogamulizumab)以及攻克偏头痛的 CGRPR 单抗(erenumab)。追根溯源,这一领域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 GPCR 抗原制备的超高难度。
文章来源:百奥几何BioGeometry
若涉及侵权,请立刻联系删除